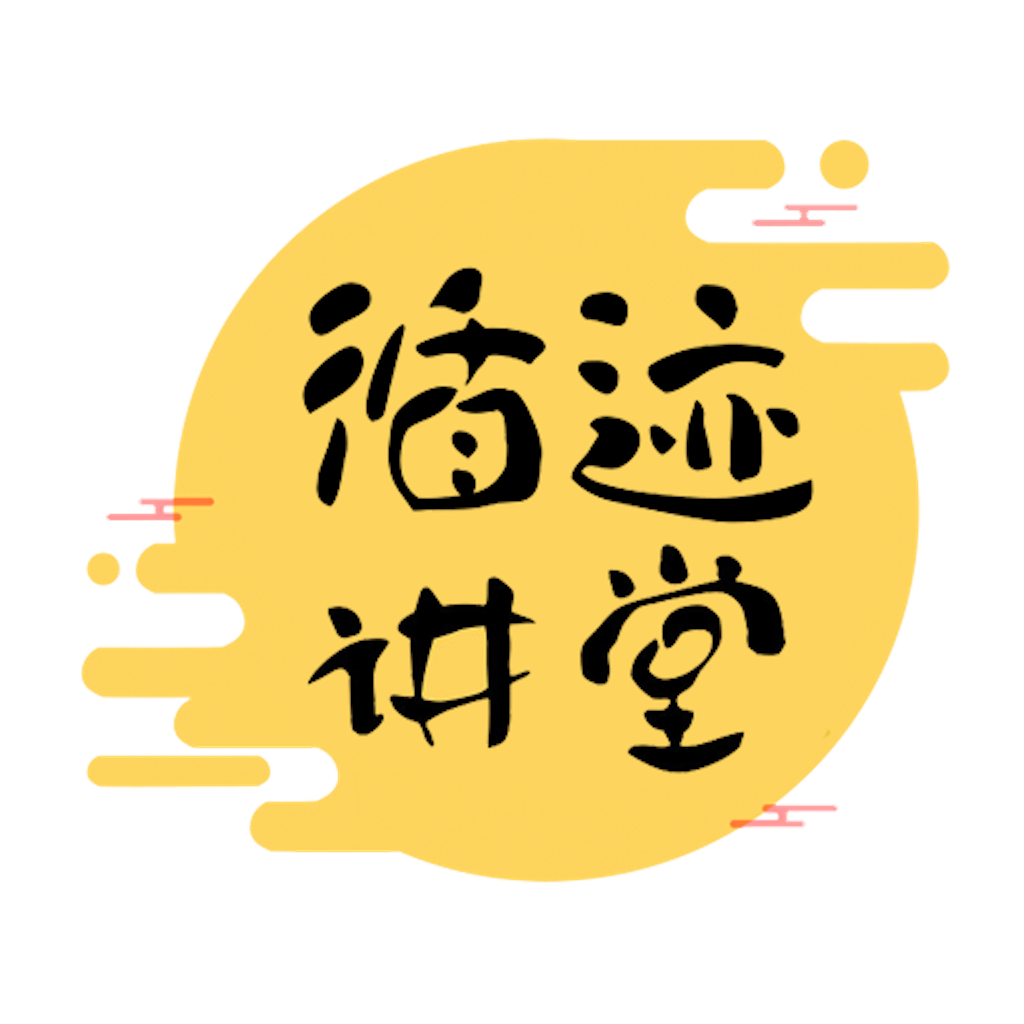2019年12月11日,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宣布瑞典环保少女格里塔当选年度人物,认为她“是一个普通的少女,她鼓起勇气向强权讲出真话,她成了一代人的偶像”。
就在格里塔赢得《时代》周刊年度人物的殊荣后没两天,小姑娘又因为一张照片惹来了大家的吐槽。
12月15日,格里塔发表了一张在德国火车上席地而坐的照片,不久之后,德铁公司(DB)立马发表声明说:“我们给了她一等座,是她自己在过道里摆拍了这张照。”

德铁还是很机智的
小姑娘除了逃学去示威、吃面包不吃面包边等等之外,在德铁上占了便宜还卖乖这事又得给她记上一笔。
话又说回来,这不是以格里塔第一次干蠢事了,为什么极端白左们总是干这种蠢事呢?
1 白左是什么?
只要满足以下几个特征基本就是我们口中的“白左”。
1.受过良好的教育;2.对少数族裔的犯罪问题和极端宗教信仰带来的社会危害选择性无视;3.对非法移民、少数族裔、LGBT群体、低收入者,抱有极大的同情心;4.主张“零排放”和“食素主义”;5.只要任何人反对或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,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。

亲如一家
而“白左”在西方世界中,在知识分子和富裕阶层中占比最多,比如:大学的教师、学生、中产阶级、最富裕的人群和企业家等等;而传统制造业的老板、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、农民等,多数是保守主义者。
首先,在笔者看来,在西方高度发达的社会体系中出现“白左”群体是非常正常的事,因为受过良好教育又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,他们天生自带圣母体质。
他们纯粹而单一的价值观让变得有别于常人,这也在正常理解范围之内。
但是,白左群体中的“极端白左”则超出了“正常”的范畴,极端白左=正常人+白莲花+黑莲花+绿茶婊+偏执狂+妄想症。

高举标语欢迎难民白左们
极端白左在日常生活中会以正常人的形态出现,他们最主要的形态就是一旦看见“受灾受难(不管他们为何受难)”的人,就会自动化身白莲花,在西方以圣母的形态出现,在东方以观音的形态出现,给予“受灾受难”的人们怜悯的泪水和帮助。
有时候,你真分不清他们是“同情心泛滥”,还是真把别人的痛苦看成自己的痛苦?
我们来看看极端白左们干过哪些蠢事。

为了老鼠屎,牺牲自己和别人
2016年,一个24岁的德国左翼党青年组织负责人,被三个难民性侵。按说,正常的反应一定是报警抓人。
可这位德国受害人偏不,在她眼里“难民们已经很可怜了,温饱都成问题,还在德国遭受种族歧视”。
为了不让难民群体遭受德国民众的诘难,于是,受害人告诉警察:“这事不是难民干的,而是三个本地人”。
但是,事件的真相还是被调查了出来。
真相曝光后,受害人担心难民因为强奸罪遭受更多的排挤,居然在网上发了一封公开信,这封信上说:“我最伤心的事情不是被性侵,而是我的遭遇,使你们这些难民遭受到更多的种族歧视”。
这封公开信中不仅没有对犯罪分子有一丝谴责,而且她还认为自己犯了什么不可原谅的罪行。

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向反对赔偿恐怖分子奥马尔的民众解释
还有更让人震惊的,加拿大公民奥马尔·卡德尔(Omar Khadr),因在未成年时被塔利班洗脑,继而参加了该组织,并与加拿大的盟友作战时被捕,期间因没有得到加拿大政府对于他基本公民权益的重视,而获得加拿大政府的公开道歉和1050万加元(5500万人民币)的赔偿金额。
然而事情的真相是,在卡德尔未成年时,他就被自己的父亲送到阿富汗塔利班的“少年成长营”接受训练和洗脑。
并在2002年用手榴弹炸死了美国士兵肖恩·克里斯托弗·斯佩尔(Sean Christopher Speer),炸伤美国士兵莱恩‧莫里斯(Layne Morris),导致莫里斯失明。
随后,当时15岁的卡德尔受伤被捕,然而加拿大政府一直不愿引渡卡德尔,才让他在关塔那摩监狱里呆了十年。

拿到赔偿的卡德尔
出狱后,25岁的卡德尔就一直与加拿大政府在打官司,大约两年前,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政府官员未能保护卡德尔免受美国监狱的虐待。
法院裁决加拿大政府向卡德尔道歉,并赔偿1050万加元。

讽刺特鲁多和卡德尔的PS照片
就这样一个恐怖分子在出狱后,居然通过打官司获得了一大笔巨款赔偿。
别急着愤怒,这种例子还有。
2018年,一名索马里籍的强奸犯被英国驱逐出境,但在飞机起飞前,整个飞机的乘客(极端白左)以为他是受迫害而流亡的难民,于是群起施压,成功逼迫负责押解他的官员带他下机。

关于索马里强奸犯的新闻
当年强奸案的受害人接受采访时不仅怒斥这些乘客的无知,而且已经绝望,只想离开英国过正常生活。
我们不去评价以上极端白左们的这些行为到底高不高尚,他们干的这些蠢事至少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坏处,那就是让危险的罪犯逍遥法外,间接增加了其他人的受害几率。
在他们以为维护“少数人群”的正义的时候,却往往把其他无辜者置于危险的境地。
2 极端白左的真面目
极端白左们号称关爱弱者和穷人,但他们每到南美的贫民窟、非洲大地摆拍作秀时,却要求当地人维护原生态的文化和环境;他们拍摄的无数主角是黑人和底层小人物的励志鸡汤电影;但他们自己却躲在精英富人社区,一边让孩子上着常青藤学校,一边高谈阔论,表达着对穷人廉价的怜悯。

非洲打卡成功
极端白左们擅长利用政治以及舆论资源,并占据道德制高点,把自己扮演成“圣母”,他们真的关心这个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吗?
不,他们只关心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世界。
就像本文开篇提到的16岁的瑞典环保小将——格里塔,在联合国上呼吁在未来10年内,全球应该实现“零排放”。
这个建议如果真的实行,就意味着全人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取缔燃油车、飞机停飞、所有烧煤的火电厂停止运行、把所有的牛杀光、所有人都改吃素。
但这种极端脑残的言论,却得到了西方媒体的高度评价。

格里塔获得CNN的高度评价
从2018年起,格里塔发起“Friday for Future”运动,号召全球青少年每周五不上学,逼迫成年人关注气候问题。
格里塔自己辍学在家,不仅组织同学示威,还带头在瑞典国会大厦前静坐,对大人们无法阻止全球变暖表示“强烈不满”。

格里塔在瑞典国会大厦前的活动
这个小姑娘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“极端白左”自我感动、自我陶醉的故事。自以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言论,进而可以拯救世界。
但这样的作秀,骗的了自己,却骗不了明白人。
3 一种传播性极强的病毒
事实上,一个文明的进步和繁荣,不仅仅有赖于她物质力量的强大,更有赖于正常的道德伦理。
一个鼓励好吃懒做的社会,是不可能进步的;一个向往虚幻美好的文明,是不可能维系的。
“白左”这个群体并不能用“坏”来形容。

格里塔和她的小伙伴们
他们的某些主张带有进步主义色彩,比如推动社会平等、鼓励多元文化、各族裔相互包容等等。“白左” 坚信“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,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”,然而满怀美好梦想的他们在现实中却经常碰壁。
一旦碰壁,白左群体中的极端群体就会恼羞成怒,认为是有人在迫害他们,阻止他们实现拯救人类的伟大理想。
这种极端的“救世情怀”一旦蔓延开来,就会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,最后不仅害人而且害己。
我们并不是反对环保主义、反对保护弱势群体,我们讨论和关心的是如何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推进环保工作,妥善有效的保护弱势群体或帮助难民。

为了所谓政治正确,迪士尼《小美人鱼》的主演选择黑人演员
比如:在面对不断涌向欧洲的难民时,他们最应该做的就是:该救助则救助,该遣返则遣返,而不是实施不加甄别的难民收容政策。
我们真正反感的是极端白左们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、反感的是他们在罪犯面前无原则的同情、反感的是他们自以为占领了道德高地就可以为所欲为。
当极端的“政治正确”已经影响到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和正常生活时,我们应该想想,一个连“政治不正确”都不能包容的社会,它还有什么资格宣扬自己是“正确”。
(完)
参考资料:
Jordan Peterson, Maps of Meaning: The Architecture of Belief
Chenchen zhang,open democracy,The curious rise of the ‘white left’ as a Chinese internet insult